非你所想的泰国

青年陈子鸿(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泰国人)在泰国古都大城阿瑜陀耶王朝遗迹参观。该照片入选 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青年眼中的亚洲多元文明”摄影作品展
文/《环球》杂志记者 凌朔
编辑/刘娟娟
今年是中国与泰国建交50周年。50年前,当新中国与泰王国在世界风云中拨开迷雾、共同掀开两国现代双边外交的扉页,新华社记者同步启程,踏上了常驻曼谷的历史长路。上百名新华社常驻曼谷分社记者前赴后继,用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努力寻求对外部世界的准确解读,努力构建关于认知邻国的真实向度。
那些看似尘封的新闻,早已凝练成厚重的历史:中泰建交前为何也有乒乓外交?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投资中国的为何是泰国企业?访华数十次的泰国公主为何如此迷恋中国?泰国这个“黄袍佛国”为何委托中国制作诸多佛造像?八年的泰越战争因何鲜为人知?泰柬又有几多恩与怨?……
作为曾经常驻泰国的新华社记者中的一员,今年5月,面对来华访学的数十名泰国新闻官员和新闻记者,我用上百张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新闻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新闻故事,讲述了中国记者视角下的泰国半世纪发展历程。课后,有学员潸然落泪,他们说,未曾想中国媒体竟然如此客观、全面、平视地记录着他们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而几十年来泰国媒体在西方新闻观的指引下一直忙于“利益的攻讦”。
严肃新闻,总是以真实为生命,以核证为流程,以渲染、夸张、片面为禁忌。也许,这些耗时费力却必要的工序在新媒体时代为许多“内容创作者”所不屑,因而才有了许许多多关于泰国的“新故事”与“新传说”,例如一度疯传的“噶腰子”。更让人遗憾的则是,传谣易、证伪难;偏见易、概全难。
泰国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我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反复观望,反复接触,积年思考,也很难总结。但我所知道的是,这个东南亚唯一一个从未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在思想深处,有着相对而言最为连贯的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与借鉴。在泰国,有人把儒学与道学研究奉为顶流;关公的忠义和包公的铁面无私家喻户晓;华人与泰人融合到算不清所占人口比例;甚至能找到在中国都已消失的中国古代节日;学中文、看中医早就不是新鲜事——20年前,一位泰国寺庙住持跟我打趣说,现在连庙里的沙弥都在学中文,敲钟都敲出了中国味道。
当然,泰国也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到沸沸扬扬的街头政治,小到司空见惯的社会怪象。今年2月,时任泰国总理佩通坦在接受我采访时着重谈了泰国应对网赌电诈的诸多举措,她最后说:“我来中国,就像回家。我也真心希望中国人多去泰国走动,看看泰国的积极变化。”
用积极的眼光,从发展的维度去看待和接触不同的事物,才是不同文明交往的便道与捷径。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后返美时,经停泰国首都曼谷。在一场早餐会上,泰国年轻的外交官德·汶纳从基辛格的眼神里察觉到尼克松政府正在接触中国,感觉到国际和地区形势剧变的前奏。在中泰双方共同推动下,两年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泰国。又过了两年,中泰正式建交,德·汶纳成了泰国首位驻华大使。10年前,在中泰建交40周年之际,在泰国外交界德高望重的德·汶纳告诉泰国领导人,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非常需要泰国的话,那么今天,泰国人需要思考的是,泰国是否还在中国的视线中。
而事实上,千百年来泰国从来都没有偏离过中国的视线。今天,每年都有数百万中国人赴泰旅行、投资、创业、康养,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古人一样,记述着他们认为“非你所想”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在诠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道理。
在这种交流中,只要我们去深究,常会发现历史的回响——当今天许多中国人飞抵曼谷、降落在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素万那普”原本的意思,是“黄金遍地”,而这个词,早在约1800年前就被三国时遍访中南半岛的吴国使臣朱应记录在《扶南异物志》中,当时的名称,叫“金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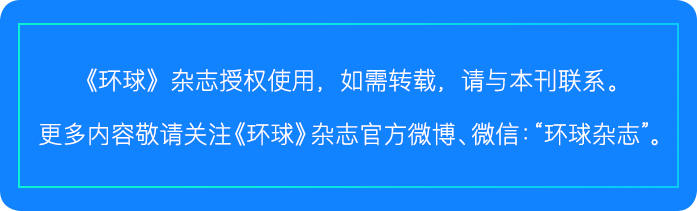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