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难民:故土上的陌生人

6月15日在阿富汗坎大哈省塔赫塔普勒地区的安泽吉难民营拍摄的坐在车里的孩子们
文/《环球》杂志记者 李昂 聂新宇(发自喀布尔)
编辑/吴美娜
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斯平布尔达克口岸,超过40℃的烈日高温下,45岁的阿富汗难民米拉·扬刚完成归国登记。他在巴基斯坦生活了41年,如今与家人和亲戚共计26人一同返回了阿富汗。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对自己将“像陌生人一样”回国生活感到“不知所措”。
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11区老城的难民营,刚从阿富汗西南部普勒阿卜里沙姆口岸和东部托尔哈姆加特口岸入境归国的难民被大巴转运到这里,接下来去往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代表贾迈勒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2023年9月以来,已有逾300万名阿富汗人从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返回,但当前的阿富汗基本不具备接纳这些归国难民的能力。他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指出,阿富汗约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而联合国估计该国有一半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被迫逃亡若许年
阿富汗是全球主要难民输出国之一,主要原因是在最近的40多年里阿富汗接连遭外国入侵,与此相伴的还有阿内部不同种族和政治派别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
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底层民众选择逃往国外。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境内第一大族群、主要聚居在阿南部地区的普什图族难民通常越过南部和东部边境线逃往邻国巴基斯坦,因为在巴北部地区,有着比在阿富汗境内人数还要多的普什图人。
造成这种“一族跨两国”现象的,是19世纪英属印度屡次入侵阿富汗后强行划定的杜兰线。这条边境线令阿富汗人特别是普什图人非常反感,导致阿巴边境地区的边防部队时常发生擦枪走火事件。
主要生活在阿富汗中北部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等阿其他民族的难民,因为他们所讲的达利语和伊朗的波斯语相似、与伊朗人生活习惯相近,主要跨过西部边境线逃往伊朗。
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这些难民的境遇因此更显无奈。据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估计,截至6月中旬仍有约700万阿富汗难民滞留海外。这些难民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
伊朗政府今年3月作出决定,要求所有无证件阿富汗人离开伊朗。而在伊朗和以色列最近爆发军事冲突后,每天从伊朗回国的阿富汗难民人数从约5000人猛增至近3万人。国际移民组织在6月的一份报告中称,今年已有70多万阿富汗难民从伊朗返回阿富汗,其中6月就有25.6万人。该组织警告说,阿富汗支持系统不堪重负,面临巨大压力。

这是2月12日在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的托尔哈姆加特边境口岸拍摄的难民
童叟命运皆揪心
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法希姆一家五口近期刚刚结束在巴基斯坦长达两年的漂泊,回到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目前暂时居住在托尔哈姆加特边境口岸附近。
“许多难民已一无所有,我们期待能获得更多援助。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衣物、食品和住所。”30多岁的法希姆站在一顶印有中英文“中国援助”的帐篷旁,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他的家乡在阿富汗巴格兰省,那里极为贫困,让他倍感无奈——既无栖身之所,亦无可耕种的土地。但他对重建生活仍充满憧憬,谈吐间透露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托尔哈姆加特边境口岸位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靠近巴基斯坦。站在口岸附近,记者目之所及,难民中有一大半是未成年人——阿富汗普通家庭大多有4个或更多孩子。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始终是个难题。
28岁的难民阿萨德有4个孩子。在巴基斯坦避难期间,他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经历了种种艰辛。如今回到祖国,他急切希望能尽快过上正常的日子。“我打算先给家人盖房子,然后当一名砖窑工人。”
但更紧迫的是生存。在托尔哈姆加特口岸,要先学会辨识地雷和其他路边潜在的爆炸物,每一个归国难民都要接受相应的短时培训。此外,联合国难民署还专门为妇女设立了女性求助点。
在坎大哈省塔赫塔普勒地区的安泽吉难民营,18岁的玛丝图拉站在尚未卸下行李的货车旁边。她刚结束在巴基斯坦14年的异国生活回到祖国,尽管继续求学的希望渺茫,她仍期盼改变:“如果无法接受教育,我必须要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也许开个小缝纫店,或者和父亲一起种地。”
在伊朗当了多年难民的穆罕默德·哈桑带着8名家人,6月徒步经由位于阿伊边境城市扎兰季的普勒阿卜里沙姆口岸返乡。面对记者,他感慨道:“我们在伊朗生活多年,遭遇了很多难民特有的困境,但同时我们也对伊朗普通民众心怀感激。”他希望阿富汗临时政府能为孩子们提供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样我就不必再次背井离乡了”。
与哈桑相比,记者见到的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被重疾击垮的阿富汗难民,更有甚者,躺在棺木里被家人朋友们用板车推着跨过了边境线。

6月15日,在阿富汗坎大哈省塔赫塔普勒地区的安泽吉难民营,一名少年从中国援助的帐篷里走出
人道危机在蔓延
为应对归国难民面临的种种困难,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提供临时住所、食物、清洁饮水、医疗援助及返乡交通等基本服务。
不过,仅靠阿富汗自己,显然无法消纳这些蜂拥而至的归国难民。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任期延长一年至2026年3月17日。决议重申对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坚定承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援助力度,重申帮助阿富汗重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等。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驻地位于喀布尔市中心,那里有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多个援助类组织的在阿分支机构,他们的共同希望是帮助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上重建道路。
国际移民组织在6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阿富汗归国难民的家庭数量急剧增加。这与前几个月的情况不同,当时,大多数回国者是年轻单身男性。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说:“遣返人数之多令人深感震惊。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强有力、更迅速的应对措施。阿富汗无法独自应对这一问题。”
国际移民组织6月底的数据显示,2025年人道主义需求和应对计划要求提供24.2亿美元的资金,但迄今为止仅到位22.2%。阿富汗已经深陷经济崩溃,长期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并未准备好应对如此大规模的难民回流。
尽管联合国难民署正奋力解决归国难民对食物、水、住所和安保等的紧急需求,但由于资金有限,项目面临巨大压力,因此不得不大幅减少对阿富汗归国难民家庭的现金援助,援助从每户2000美元已减少到仅156美元。联合国难民署表示,2025年该机构在阿富汗的紧急援助行动共需2.16亿美元资金,但目前仅筹得约四分之一。它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增加投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阿富汗事务负责人伊莎贝尔·卡尔森说:“在预测到危险之前采取行动,防止或减轻因人道主义援助不足对社区造成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全球和阿富汗的人道主义行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每一块钱。”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拨款170万美元,用于支持法里亚布省受旱灾影响的家庭——这笔资金将向该地区约8000个家庭提供现金援助。该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已经面临危机或达到紧急程度的严重粮食不安全。

6月17日,在阿富汗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季市与伊朗接壤的普勒阿卜里沙姆口岸,阿富汗归国难民进行入境登记
点滴关切在心头
在阿富汗,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普遍对在这里的中国人态度友善。在喀布尔,阿富汗人常常用中文“你好”向记者打招呼。
今年是中阿建交70周年,在阿富汗人民面临人道主义危机时,中国人民给予了这个邻邦及时的关心与支持。
记者第一次见到印有“中国援助”“CHINA AID”中英文字样的救灾帐篷是在托尔哈姆加特口岸,之后在普勒阿卜里沙姆口岸、斯平布尔达克口岸,以及在安泽吉难民营、喀布尔难民营也都见到过。每次看到这些蓝色的中国援助救灾帐篷,就让人感到特别心安。“抗风”“隔温”“防潮”,难民对这些帐篷有着高度的好评。
“中国此前曾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包括整车的粮食和帐篷等,我们深表感激。”尼姆鲁兹省难民事务与遣返管理局负责人毛拉维·阿卜杜拉·雷亚兹面对来自中国的记者,对中国给予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诚挚感谢。
阿富汗临时政府难民和遣返事务部发言人阿卜勒·穆塔利布·哈卡尼说:“我们衷心感谢中国在关键时刻给予援助,尤其是在大量阿富汗难民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返回的时期。中国的援助恰逢其时,我们对中国深表感激。”哈卡尼表示,安置归国者的挑战巨大,而中国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邦,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急需物资,包括帐篷、毛毯、车辆、救护车和水罐车。这些物资已分发至各大边境口岸,为处于困境中的阿富汗难民雪中送炭。
此外,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也积极联络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阿富汗红新月会等国际和本地援助组织,向不同群体提供援助。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代表阿拉法特·贾迈勒说:“我们十分感谢中国提供的重要援助,这帮助我们在困难时期为流离失所的阿富汗家庭提供支持,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当阿富汗面临洪水、地震、干旱和雪灾等自然灾害时,中国也及时施以援手。2024年,阿富汗多地发生严重洪灾,中国向当地红新月会捐资援助受洪灾影响的家庭,并迅速向受灾地区的数千户家庭分发小麦、豆类、毛毯、衣物、药品等救援物资。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6月23日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保持同阿富汗临时政府对话接触、加大对阿人道援助,将对阿富汗人民的关心落到实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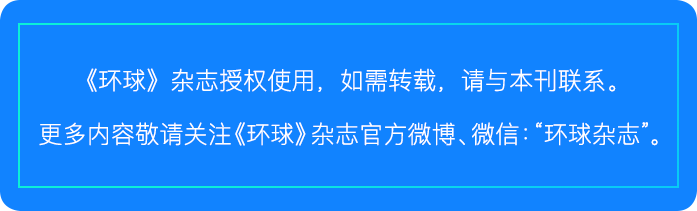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